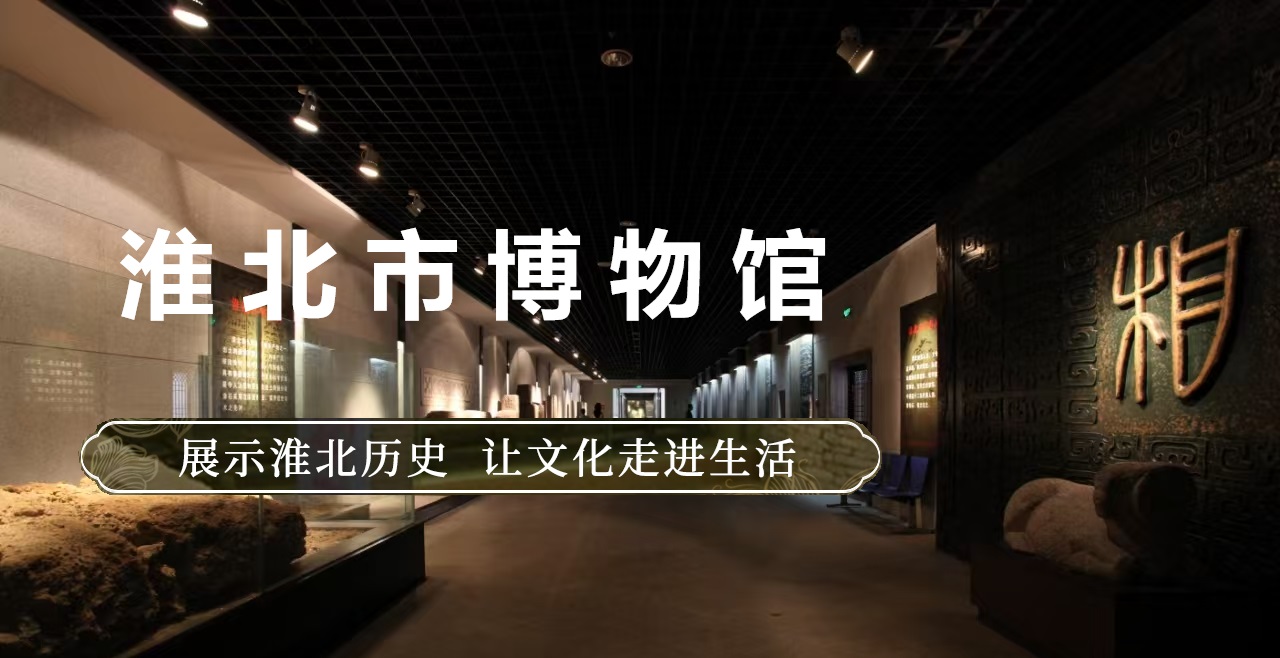圖為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出土玉器。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要實(shí)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xiàng)目。2020年“考古中國”連續(xù)發(fā)布了四期共16項(xiàng)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加上2018年和2019年的重要項(xiàng)目,共有31項(xiàng),內(nèi)容非常豐富,新發(fā)現(xiàn)新突破很多,令人振奮。
“考古中國”重大項(xiàng)目有哪些特點(diǎn)?在“十四五”的開局之年將有哪些新的舉措?本報(bào)記者采訪了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
記者:“考古中國”重大項(xiàng)目近幾年進(jìn)展很大,重要發(fā)現(xiàn)很多,大家都很關(guān)注它的相關(guān)情況。
宋新潮:“考古中國”重大項(xiàng)目在《國家文物事業(yè)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中首次提出,主要以考古和多學(xué)科、跨學(xué)科合作研究為主要手段,重點(diǎn)組織實(shí)施中國境內(nèi)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中華文明形成、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fā)展、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關(guān)鍵領(lǐng)域考古項(xiàng)目,全面、科學(xué)地揭示中華文明歷史文化價(jià)值和核心特質(zhì),探討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規(guī)律,促進(jìn)文明比較研究,以考古學(xué)實(shí)證中華文明發(fā)展歷程,凝聚民族共識(shí),堅(jiān)定文化自信。
項(xiàng)目立足考古研究。以考古學(xué)理論、方法構(gòu)建中國境內(nèi)人類演化、社會(huì)發(fā)展、國家形成的百萬年漫長歷史,依托田野考古實(shí)踐和考古出土各類實(shí)物資料講述何以中國、何為中國,為更好認(rèn)識(shí)源遠(yuǎn)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提供科學(xué)的學(xué)術(shù)支撐。
聚焦重大問題。這些重大項(xiàng)目緊扣考古事業(yè)發(fā)展和考古學(xué)科建設(shè)的關(guān)鍵領(lǐng)域和重點(diǎn)方向,多角度探索古代政治、經(jīng)濟(jì)、科技、環(huán)境、地理、精神與宗教,深入挖掘考古遺址和文物遺存背后蘊(yùn)含的中國哲學(xué)思想、人文精神、價(jià)值理念、道德規(guī)范等,從歷史的長鏡頭探尋中華文明形成、發(fā)展、壯大的客觀規(guī)律和內(nèi)生動(dòng)力。
通過這些項(xiàng)目,促進(jìn)考古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深度融合,發(fā)展古DNA研究、測年技術(shù)、動(dòng)物考古、植物考古、環(huán)境考古等交叉學(xué)科、新興學(xué)科,提高考古學(xué)的發(fā)現(xiàn)、分析和解讀能力,加強(qiáng)考古能力建設(shè)和學(xué)科建設(shè)。
記者:從2018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加大了對(duì)“考古中國”重大項(xiàng)目的指導(dǎo)、協(xié)調(diào)和發(fā)布, 這些項(xiàng)目給考古研究帶來了哪些變化?
宋新潮:“考古中國”在“十三五”期間協(xié)調(diào)國內(nèi)考古機(jī)構(gòu)、科研院所和高校組織主要開展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區(qū)聚落與社會(huì)研究”“長江下游地區(qū)文明化進(jìn)程研究”“長江中游地區(qū)文明化進(jìn)程研究”“中原地區(qū)文明化進(jìn)程研究”“海岱地區(qū)文明化進(jìn)程研究”等10項(xiàng)重大項(xiàng)目。
過去我們對(duì)于距今八九千年的文明發(fā)展程度了解不多,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河北康保興隆遺址,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距今8000多年我國北方地區(qū)較早的定居性聚落,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的發(fā)現(xiàn),為中國北方地區(qū)粟黍馴化和旱作農(nóng)業(yè)起源提供了重要證據(jù)。近年來發(fā)掘的距今9000年的浙江義烏橋頭遺址以及距今8300—7800年的浙江余姚井頭山遺址,進(jìn)一步豐富了我們對(duì)于長江下游地區(qū)稻作文明的認(rèn)識(shí)。井頭山遺址更是中國近海地區(qū)迄今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開發(fā)海洋資源、適應(yīng)濱海生活提供了新資料。
夏時(shí)期的考古過去局限于豫西、晉南等地區(qū),通過“考古中國”,現(xiàn)在已經(jīng)擴(kuò)展到山東、安徽、陜西乃至江漢平原。比如在長江中游地區(qū),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考古,初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間石家河遺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變過程,揭示了長江中游地區(qū)新石器時(shí)代晚期、特別是進(jìn)入夏時(shí)期的肖家屋脊文化的面貌。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也是一處新石器時(shí)代末期至夏代早期的遺址,總面積超過22萬平方米,文化堆積豐富,為認(rèn)識(shí)新石器時(shí)代晚期到夏商階段中原地區(qū)與長江中游地區(qū)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線索。
“考古中國”重大項(xiàng)目還開展了絲綢之路考古、邊疆考古。有趣的是,2019年的甘肅天祝祁連鎮(zhèn)岔山村唐墓和2020年青海都蘭熱水血渭一號(hào)墓,出土了豐富的歷史文物。都蘭熱水血渭一號(hào)墓發(fā)掘出土的印章,屬于吐蕃文字,釋讀為“外甥阿柴王之印”。“阿柴(A—Za)”是吐蕃人對(duì)吐谷渾的稱呼。吐蕃為了對(duì)吐谷渾進(jìn)行控制,長期保持王室的聯(lián)姻,從而形成了特殊的“甥舅關(guān)系”。這枚印章不僅印證了其它出土文獻(xiàn)的記載,而且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與族屬。從天祝唐墓出土墓志,可以肯定墓主人是武周時(shí)期吐谷渾王族成員喜王慕容智。慕容智是歸附唐王朝的吐谷渾王族,其墓志用漢字書寫,但發(fā)掘者在其志石一側(cè)發(fā)現(xiàn)兩行未識(shí)的文字,很可能是利用漢字創(chuàng)造的民族文字。
記者: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 “考古中國”重大項(xiàng)目會(huì)有哪些新的布局?
宋新潮:2021年我們想著力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以舊石器時(shí)代考古、巴蜀文化研究、南島語族考古、夏商考古、石窟寺考古等為重點(diǎn),集中力量解決一些重大問題。第二,加強(qiáng)專業(yè)隊(duì)伍建設(shè),增強(qiáng)科技考古力量。國家文物局新成立的考古研究中心將創(chuàng)新體制機(jī)制,增強(qiáng)考古工作的科技含量。第三,加強(qiáng)國際合作,在國際合作交流中增強(qiáng)中國考古的話語權(quán)和影響力。第四,關(guān)注遺址保護(hù)。我們將同地方政府合作,及時(shí)把新發(fā)現(xiàn)的重要遺址公布為相應(yīng)級(jí)別的文物保護(hù)單位,加大保護(hù)力度。
(《人民日?qǐng)?bào)》記者 王 瑨;2021年01月09日第5版)
來源:國家文物局網(wǎng)站

淮北市博物館微信公眾號(hào)

監(jiān)督一點(diǎn)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