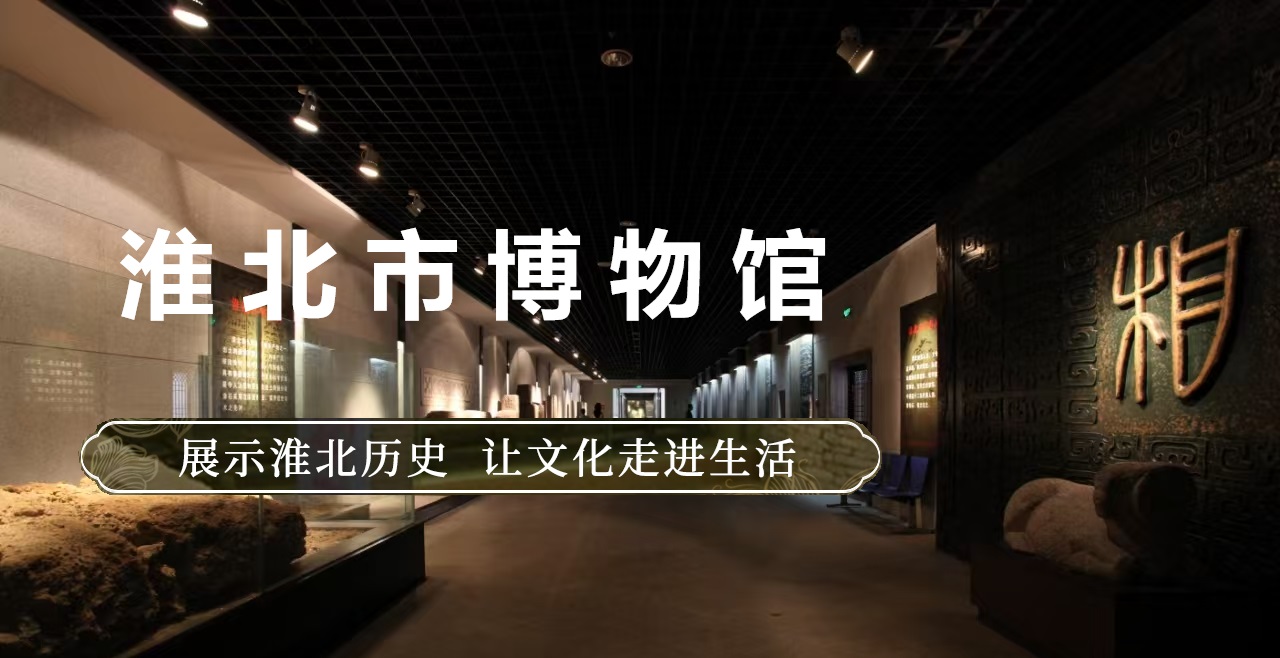2021年之于中國考古,是特殊的一年,又別樣的忙碌。特殊,因為這一年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xué)誕生100周年。忙碌,在于廣大考古人依舊日復(fù)一日,勤勤懇懇、默默耕耘,奔走在廣袤的大地上、田野間。
在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和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xué)誕生100周年之際,習(xí)近平總書記發(fā)來賀信,代表黨中央向全國考古工作者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總書記的賀信對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xué)百年以來的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對中國考古學(xué)之于歷史研究、之于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發(fā)揮的重要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考古界和各文博單位備受鼓舞。
“對歷史的最好紀念,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如今,這片古老的土地?zé)òl(fā)出新時代的風(fēng)采,見證中國考古迎來黃金時代,中國考古人向著“十四五”新征程和新百年發(fā)展目標(biāo)整裝再出發(fā)。
傳承百年榮光 譜寫中國考古新篇章
1921年10月,河南省澠池縣仰韶遺址發(fā)掘,揭開了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xué)的序幕。百年之際,全行業(yè)、全社會舉行了豐富多彩的紀念活動,掀起全社會關(guān)注考古、全民參與成果分享的文化熱潮。
為系統(tǒng)回顧中國考古百年光輝歷程,全面展示中國考古百年偉大成就,2021年年初,中國考古學(xué)會、中國文物報社與有關(guān)考古文博單位共同發(fā)起了紀念“中國考古百年”系列活動。作為系列活動的重要內(nèi)容,在國家文物局指導(dǎo)下,中國考古學(xué)會、中國文物報社組織開展了“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遴選推介活動”。各地文物部門積極組織,踴躍參與,共有來自全國34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337項發(fā)現(xiàn)申報,最終產(chǎn)生了100項“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和5項考古遺址保護展示優(yōu)秀項目。與此同時,湖南、河南、山東、河北、湖北等地也紛紛開展了省內(nèi)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出土文物精品、經(jīng)典考古報告的評選活動,與“百年百大發(fā)現(xiàn)”遙相呼應(yīng),為系列活動添磚加瓦。
由國家文物局指導(dǎo),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中國文物報社共同策劃主辦了紀念中國考古學(xué)誕生100周年系列公開課“中國考古大講堂”。大講堂以中國考古事業(yè)發(fā)展歷程為主線,通過11場專題講座,針對中國考古學(xué)科建設(shè)的關(guān)鍵領(lǐng)域和重點方向進行了深入解讀,引導(dǎo)觀眾發(fā)現(xiàn)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的歷史脈絡(luò)。此外,故宮博物院考古部、故宮考古研究所也推出系列講座,邀請知名學(xué)者回顧中國考古學(xué)百年歷程,講述考古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重要研究與收獲。
一年來,全國各地的考古院所和博物館陸續(xù)推出了一系列紀念中國考古百年的相關(guān)展覽,這些展覽分量重、角度新、地域特色明顯。其中有反映地方考古事業(yè)發(fā)展的綜合性展覽,比如重慶市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特別策劃的“重慶考古百年展”、在山東博物館展出的“山東考古成就展”以及南京博物院策劃的“考古江蘇”;也有角度新穎,反映行業(yè)特點、特色的專題展,比如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稻·源·啟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湖北省博物館舉辦的“永遠的三峽——三峽文物保護利用數(shù)字展”,在張家港博物館舉辦的2021長江文化節(jié)主題展覽“考古里的長江文明”。
2021年是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100周年,也是山西夏縣西陰遺址發(fā)掘95周年,還是牛河梁遺址發(fā)現(xiàn)40周年。1926年,李濟先生在夏縣西陰遺址主持了由中國人獨立開展的首次考古發(fā)掘。2021年9月,“紀念中國考古100周年暨西陰遺址發(fā)掘95周年學(xué)術(shù)研討會”在山西運城召開,與會者圍繞西陰遺址與百年中國考古、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等話題進行交流。40年前,牛河梁遺址的發(fā)現(xiàn)點燃了學(xué)術(shù)界對紅山文化研究的熱情。2021年10月,在紀念牛河梁遺址發(fā)現(xiàn)40周年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與會學(xué)者圍繞紅山時代地域文明的發(fā)展、碰撞與交流,中華文明基因中的紅山因素,多學(xué)科視角下的紅山文化研究展開討論。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暨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xué)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舉行,大會宣讀了習(xí)近平總書記賀信。這是中國考古學(xué)界的一次盛會,也使紀念考古百年的系列活動達到高潮。習(xí)近平總書記的賀信,令廣大考古人心潮澎湃,深受鼓舞,倍感振奮,各地紛紛掀起學(xué)習(xí)宣傳貫徹的熱潮。回望百年考古,致敬考古先賢,是為了步履堅定地建設(shè)中國特色、中國風(fēng)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xué),使下一個百年的中國考古學(xué)研究更上一層樓,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
考古看見中國 探源思索文明
“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以下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學(xué)術(shù)課題的實施,已經(jīng)成為中國考古學(xué)發(fā)展的強勁推動力,不但肩負著探究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重任,同時也承擔(dān)著增強民族自信心的重任。我們從哪里來?何以中國?何以華夏?考古以實證解決了我們的疑問。圍繞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揭示本源 探索未知”的要求,設(shè)置了一批重大研究課題,圍繞課題開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21年,國家文物局分別于3月20日、6月8日、9月27日、10月15日、12月1日、12月14日召開6次“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新進展工作會,共發(fā)布15項重要考古成果。北京市懷柔區(qū)箭扣長城、陜西省靖邊縣清平堡、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遺址3項長城考古的重要發(fā)現(xiàn),生動展現(xiàn)了長城作為古代軍事防御體系的建筑遺產(chǎn)價值,以及長城沿線地區(qū)文化、民族的頻繁交流與融合;從稻城皮洛遺址已發(fā)現(xiàn)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shù)產(chǎn)品,到沂水跋山遺址出土距今9.9萬年的象牙鏟,再到魯山仙人洞遺址發(fā)現(xiàn)的3.2萬年前現(xiàn)代人頭骨,3項舊石器重要發(fā)現(xiàn)涵蓋了南北方、東西部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考古研究內(nèi)容;隴原大地上,分布排列有序聯(lián)排房址的南佐遺址和擁有三重環(huán)壕的圪垯川遺址,實證了甘肅東部黃土高原是仰韶文化又一核心;無論是現(xiàn)身崇禮的“河北第一城”鄧槽溝梁遺址、見證滄海桑“田”的施岙遺址,還是被證實為漢文帝霸陵真身的江村大墓、正平坊遺址內(nèi)疑似的太平公主宅院、生動揭示歸唐吐谷渾人的武威吐谷渾墓葬群……經(jīng)過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令人驚訝的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層出不窮,不但建立起歷史的時空框架,更豐富了歷史的脈絡(luò)與枝葉,在探尋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脈絡(luò)中意義重大。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豐富且扎實。2021年,在浙江北距良渚古城2公里左右的良渚早期聚落遺址——北村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良渚文化貴族大墓;一鳴驚人的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揭露出一批屈家?guī)X文化時期的木構(gòu)建筑,其等級之高、結(jié)構(gòu)之規(guī)整、保存之完好,實屬罕見;陶寺遺址宮城內(nèi)發(fā)現(xiàn)了面積達630余平方米的宮室類單體建筑遺跡,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發(fā)掘與發(fā)現(xiàn),對于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以及早期中國等重大課題研究具有推動意義。
三星堆遺址新一輪發(fā)掘始終秉持“課題預(yù)設(shè)、保護同步、多學(xué)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工作理念,在發(fā)掘方法和手段上根據(jù)各坑實際情況制定了不同的填土解剖發(fā)掘方案,記錄方面采用田野考古信息系統(tǒng)和現(xiàn)場標(biāo)簽打印為依托的數(shù)字化記錄模式,可謂“盡精微”;聯(lián)合國內(nèi)39家科研機構(gòu)、大學(xué)院校以及科技公司,組織不同領(lǐng)域的知名專家擔(dān)任學(xué)術(shù)顧問,“80后”和“90后”年輕人擔(dān)重任,構(gòu)建起了覆蓋面廣闊的多學(xué)科交叉工作團隊,可謂“致廣大”,是新時期中國考古學(xué)進行實踐探索的典范。
按下人才培養(yǎng)“加速鍵”多措并舉化解人才短缺難題
在當(dāng)前新形勢下,要保持考古持續(xù)高質(zhì)量發(fā)展,尚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中國考古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大量人才。2021年,國家級考古研究機構(gòu)、地方考古研究機構(gòu)和高校積極行動,各地文物考古機構(gòu)紛紛增編,考古隊伍不斷壯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等接連掛牌。
2021年5月,中國考古學(xué)會考古教育專業(yè)委員會的成立,為考古教育工作者搭建了合作交流平臺。考古人才的培養(yǎng)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高校文物考古及相關(guān)專業(yè)各個層級學(xué)生的招生規(guī)模有所擴大。
田野實習(xí)對考古專業(yè)學(xué)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這里才能真正叩開考古的門,它既是試金石也是分水嶺。2021年,國家文物局就加強考古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提高高校田野考古實習(xí)質(zhì)量制定了《高校田野考古實習(xí)方案編制指南(試行)》。同時,各高校也不斷積極建設(shè)設(shè)施完善、環(huán)境良好、科學(xué)規(guī)范的田野考古實習(xí)實踐基地。山東大學(xué)垓下考古實踐基地、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鹽池基地、北京大學(xué)(長島)考古實驗實踐教學(xué)基地相繼揭牌。在教育部2021年2月公布的第二批基礎(chǔ)學(xué)科拔尖學(xué)生培養(yǎng)計劃2.0基地名單中,吉林大學(xué)獲得首個國家考古學(xué)拔尖學(xué)生培養(yǎng)基地,增設(shè)全國第一個古文字學(xué)“強基計劃”本科專業(yè)。
為了促進考古從業(yè)者人才培養(yǎng)和隊伍建設(shè),吉林大學(xué)山西運城夏縣田野考古實踐教學(xué)基地不僅滿足了吉大考古專業(yè)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實習(xí)要求,還于2021年首次承擔(dān)了“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實踐訓(xùn)練班”的培訓(xùn)任務(wù),為壯大田野考古項目負責(zé)人隊伍做貢獻;針對佛教考古與石窟寺研究、夏文化研究遇到瓶頸,問題在于人才不足、隊伍斷檔,“夏文化考古研究”研修班和佛教考古與石窟寺研究專題研修班分別于2021年4月、10月在河南洛陽開班;應(yīng)對高校缺少專門從事舊石器教學(xué)老師、主持舊石器遺址“考古領(lǐng)隊”人數(shù)少的諸多制約因素,2021年6月舊石器時代考古高級研修班在寧夏水洞溝遺址開班。為切實提升城市考古發(fā)掘水平、深入了解城市考古的工作理念和發(fā)掘方法,繼2017年、2018年兩屆國家文物局城市考古專題研修班及2019年首屆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城市考古開放工地高級研修班之后,2021年7月,第三屆城市考古開放工地高級研修班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市巴林左旗開班。這是依托遼上京遺址開展的第五次城市考古專題培訓(xùn)班,是培養(yǎng)高層次城市考古專業(yè)人才、提升全國城市考古工作水平的重要舉措。
專業(yè)研究人員和技師隊伍的培訓(xùn)以各種形式展開,各領(lǐng)域、各研究方向?qū)W員深度參與考古工作,邊發(fā)掘、邊研究、邊討論,教學(xué)相長、以教促研,力爭學(xué)術(shù)取得新突破,更加熱愛、積極投身相關(guān)領(lǐng)域考古研究。
我們也可以看到,長期制約中國考古發(fā)展的問題如編制緊張、考古人員待遇較低等諸多問題都在逐步解決。為努力解決長期以來文物考古工作任務(wù)重、人手少、工作量大的問題,消解制約文物考古事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全面進步的瓶頸,中央編辦印發(fā)《關(guān)于加強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機構(gòu)編制保障的通知》。“十四五”期間,北京、河北、山西、浙江、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陜西等10個文物大省(市),通過在文化和旅游、文物系統(tǒng)內(nèi)部調(diào)劑或跨部門調(diào)劑,逐年增加編制的方式,將省級考古研究院(所)編制規(guī)模調(diào)劑增加到180名以上;其余省份同類機構(gòu),編制規(guī)模調(diào)劑增加到90名以上。據(jù)悉,2021年6月陜西省委編辦批復(fù)同意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加掛陜西考古博物館牌子,增加事業(yè)編制105名;浙江省委編辦已就核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事業(yè)編制事宜開展研究。杭州市委編辦在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現(xiàn)有25名事業(yè)編制的基礎(chǔ)上再核增25名事業(yè)編制。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增加事業(yè)編制5名。
“考古前置”為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shè)發(fā)展保駕護航
2021年3月,自然資源部、國家文物局聯(lián)合印發(fā)《關(guān)于在國土空間規(guī)劃編制和實施中加強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管理的指導(dǎo)意見》,要求“經(jīng)文物主管部門核定可能存在歷史文化遺存的土地,要實行‘先考古、后出讓’制度,在依法完成考古調(diào)查、勘探、發(fā)掘前,原則上不予收儲入庫或出讓。”
考古是文物保護的重要切入點,為了實現(xiàn)雙贏,破除文物保護與開發(fā)建設(shè)之間的矛盾,將考古調(diào)查勘探發(fā)掘工作前置到土地出讓或劃撥前完成,針對這一新舉措,各地全面開啟考古前置改革,出臺相關(guān)地方性法規(guī)和政策規(guī)定,從而促進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shè)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同頻共振。
河南省范圍內(nèi)“考古前置”規(guī)定普遍得到了有效實施,“區(qū)域文物影響評估”快速推廣開展;山西省推動落實“先考古、后出讓”政策,加大基本建設(shè)考古經(jīng)費省市縣三級財政保障力度,積極實踐政府預(yù)算保障體系下的基建考古新模式。
不再因為縮短工期、逃避考古,而導(dǎo)致地下文物損毀;不再因為地下遺存的突然出現(xiàn)使得項目擱置;不再因為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而被迫置換土地。讓城市建設(shè)和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讓“要動土、先考古”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實現(xiàn)城市建設(shè)與文物保護工作相得益彰。
闡釋保護利用 考古遺址融入現(xiàn)代生活
中國的“申遺”之路已經(jīng)走過三十余年。30多年里,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從無到有、由少變多,遺產(chǎn)類型不斷豐富,保護經(jīng)驗不斷積累。2021年7月25日傍晚,第44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審議現(xiàn)場傳來喜訊,“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mào)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成為我國第56處世界遺產(chǎn)。承載著關(guān)鍵價值特征的22處遺產(chǎn)要素及其關(guān)聯(lián)環(huán)境,完整地體現(xiàn)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貿(mào)易體系與多元社會結(jié)構(gòu)。
泉州申遺并非一帆風(fēng)順。此次申遺,新增南外宗正司遺址、市舶司遺址、安平橋、順濟橋遺址、德化窯址、安溪青陽下草埔冶鐵遺址6處申報點。組織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聯(lián)合福建博物院開展市舶司、南外宗正司、德化窯、安溪冶鐵遺址考古發(fā)掘和古城歷史研究,成果豐碩,更好闡釋泉州城的歷史和現(xiàn)實價值,為調(diào)整后的申報項目提供了有力支撐,最終確保“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mào)中心”申遺成功。
考古,是文物保護、研究工作的基礎(chǔ)。正如徐光冀先生所說,“申遺成功之日,不是終結(jié),而是泉州歷史考古、文化研究、保護和利用新的起點”。
2010年以來,通過建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整體保護大遺址的方式得到各界普遍認可。經(jīng)過3個五年規(guī)劃的努力,我國已經(jīng)形成了以150處大遺址為支撐的大遺址保護格局,評定公布了36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大遺址考古研究、保護管理、開放服務(wù)、隊伍建設(shè)、制度創(chuàng)新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果。
大遺址價值的發(fā)掘與闡釋,保護與利用,離不開考古研究的支撐。2021年,國家文物局印發(fā)《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guī)劃》,對未來五年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進行謀篇布局。規(guī)劃中提到,要將考古研究貫穿于大遺址保護利用全過程,不斷廓清大遺址價值內(nèi)涵,明確保護重點,豐富展示內(nèi)容,拓展傳播渠道,全面闡釋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的歷史脈絡(luò)、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的突出貢獻。
在注重遺址價值闡釋的同時,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積極融入當(dāng)?shù)厣鐣睿蔀槌鞘形幕貥?biāo)和市民休閑活動場所。規(guī)劃中也著重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分類管理、多方參與、社會共享,探索文物領(lǐng)域深層次改革,兼顧當(dāng)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推動大遺址融入現(xiàn)代生活。
2021年10月,位于河南澠池的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開園,規(guī)劃總面積約2800畝,將仰韶文化博物館、發(fā)掘紀念點、文化層斷面、考古展示區(qū)等景觀串點連線。同樣在10月,瑤山遺址公園試開園,是繼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城址區(qū))開放后的又一遺址參觀點,既是展示良渚時期歷史環(huán)境特征的區(qū)域,也是一座可游、可憩、可學(xué)的遺址公園,受到公眾普遍歡迎。
從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公布以來,經(jīng)過10多年的建設(shè)發(fā)展和深化管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經(jīng)成為人民群眾近距離感悟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重要場所,也是助力城鄉(xiāng)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文化名片,廣受民眾喜愛。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18日,四川德陽廣漢三星堆遺址管理委員會與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簽署《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聯(lián)合申遺合作協(xié)議》,雙方將在世界文化遺產(chǎn)申報與研究、陳列展覽、宣傳推廣等方面展開合作。
考古綜藝集體上新
用最炫的影像把考古發(fā)現(xiàn)真實地推送到網(wǎng)友眼里。對已經(jīng)找到社交媒體時代文化敘事策略的考古人來說,已不是難事,考古工作者在這片廣闊卻相對陌生的領(lǐng)域求創(chuàng)新、謀發(fā)展。
從聚焦考古人的紀錄片《發(fā)掘記》到力求講好考古故事的《中國考古大會》,從舞蹈《唐宮夜宴》驚艷四座再到真人版《帝后禮佛圖》迅速走紅網(wǎng)絡(luò),考古掀起的熱度一直在發(fā)酵,文化遺產(chǎn)也在更多地走進群眾生活,為我們提供豐厚的精神滋養(yǎng),增加文化自信的底氣。
公共考古的成果其實很難量化,但可見、可感,傳播讓考古研究人員的成果“出圈”,考古正以新面貌走向大眾視野,擺脫深奧冷門的刻板印象,年代久遠的文物將不再遙不可及,厚重的歷史也可以鮮活有趣。我們深切感受到,考古工作者們用心發(fā)掘的文物,正在以越來越豐富、新穎的方式“活起來”,煥發(fā)出新的時代光彩。
2021年我們與他們告別
在學(xué)術(shù)的道路上,始終有一批高擎理想明燈的人為我們指引前路。他們上下求索,為考古殿堂添磚加瓦;他們奉獻畢生,從未停止奔波的步伐;他們出身平凡,卻受人敬仰、鑄就光輝人生。
那位永遠把學(xué)生放在心上的考古學(xué)界公認“第一好人”劉緒先生、那位“吃雞”不忘拼骨的新中國第一位考古學(xué)博士王迅先生、那位終其一生不斷追問“我們從哪里來”并時刻提醒“做古人類研究要習(xí)慣爭議”的吳新智先生,還有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事業(yè)奠基人之一郭素新先生、親歷滿城漢墓考古發(fā)掘和報告編寫的鄭紹宗先生、“童心求真”論巴蜀的林向先生……
還有許久未見的同窗同門好友、在探訪中一起發(fā)掘、論文上互相切磋的同事,那個愛冒險又執(zhí)著為熱愛而活的劉拓、那個希望能夠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把科技和考古整合在一起的朱鐵權(quán)、那個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寶墩古城遺址,卻未曾見證“天府之根——寶墩遺址與寶墩文化”陳列館的何錕宇……
愿時光不忘他們的容貌,記住他們曾為考古努力奮斗的模樣,我們懷念他們。
(執(zhí)筆:張宸 郭曉蓉)